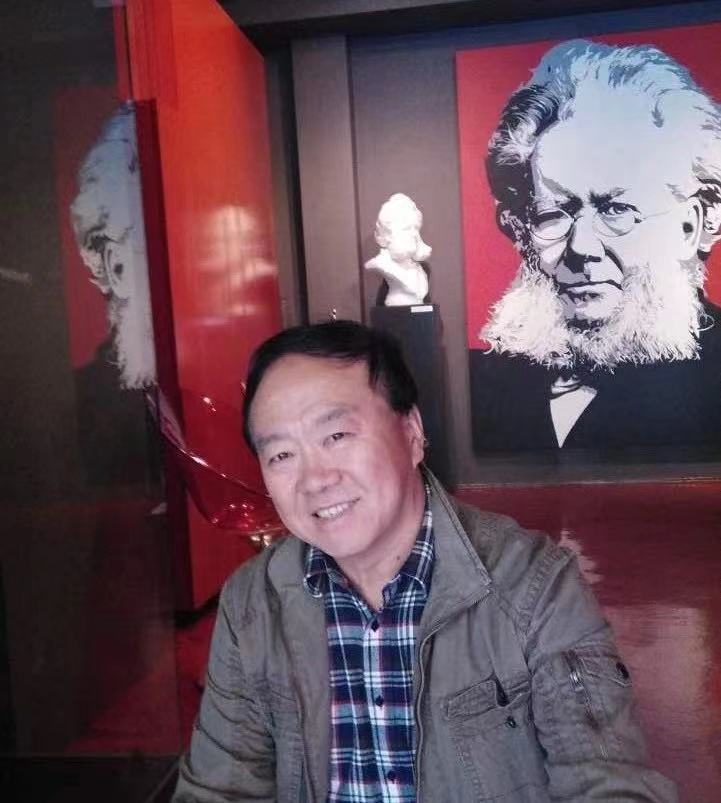
赵剑华:钢蓝色的诗意与人生
赵剑华,一级作家,内蒙古作家协会首届签约作者。现为包头市政协文学艺术院院士、包头市文艺自愿者协会副主席、包头诗词学会副会长、包头市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、内蒙古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曾任包头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。
在赵剑华的诗集《穿越》中,有一张拍摄于1988年的照片特别醒目,照片中,年轻的他头戴安全帽,朝气蓬勃,笑容灿烂,背后,是火热的生产现场。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:“钢蓝色的诗情产生于这样的背景。”在他的诗歌中,“钢铁是一个整体的概念,超出了物质的属性……钢铁整天在我们眼前流淌,溶入我们的青春和理想……”那时的赵剑华已在诗坛崭露头角,而人们所不知道是,远在这个年代之前,他便对诗歌情有独钟了。
1958年,赵剑华出生在包头一个四面环山的矿区——杨圪楞煤矿。15岁之前,他不曾走出大山,守着这无边的苍凉与落寞,他不知道外面世界的纷繁与精彩。忆往昔,赵剑华说:“我父亲是解放前在大青山背煤的矿工,解放后当了矿区的干部,文化不高,收入也不高,家里兄弟姊妹六个,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我母亲没文化,但是她坚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。而我,一直是那种梦想比较多的孩子。那时,我的理想就是上大学。”
然而,理想丰满,敌不过现实的骨感,好事总要多磨。1974年,赵剑华终于冲出大山的怀抱,来到位于东河区边缘郊外的包头市第十一中上学。他说:“这也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,尽管仍是郊区,但毕竟出了大山。”这时,赵剑华接触到了让他心动不已的诗歌。“和矿里的初中不同,十一中有图书馆,一次,我很意外地发现了一本诗集,就是贺敬之的《放歌集》。在我的印象中,那是第一次接触诗歌。其中的《雷锋之歌》《桂林山水歌》《放声歌唱》《回延安》等,每一首都深深地打动着我,我就借回去全部抄下来,诗集有200来页,收录诗歌几十首,很多是长诗,我几乎都能背下来,至今记忆犹新。后来,我又发现了李瑛的诗集《红花满山》,也特别喜欢,也是全部抄了下来。”
而好景不长,赵剑华仅仅上完高一,就被父亲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办了退学,原因是姐姐去了兵团,哥哥下了乡,家里可以给一个指标参加工作。“那时的孩子不比如今,要自我、要自由,我虽然很想上学,但是既然父亲觉得上班更有前途,那就无条件服从。”
短暂的高中时代就这样半途画上了句号,退学时,他谎称《放歌集》丢失,以双倍的赔偿价格保留了这本书,至今,它仍完好无损地置于赵剑华的案头,纪念着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。也是从那时开始,赵剑华有了刻意阅读诗歌的念头。比如曾发表于《光明日报》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1974年集体创作的长诗《理想之歌》,足足有两千行之多,他曾全部背诵。“红日,白雪,蓝天,乘东风,飞来报春的群燕……”成为他理想中诗歌的最初的底色。
回到矿里,领导们得知赵剑华学习成绩好又酷爱读书,就安排他到矿区中学当老师。“起初,我有些不愿意,但是父亲说,学校的环境适合我读书。那么,就听他的罢。后来回忆这短短的一小段经历,还真是挺难忘。”赵剑华说,是讲台锻炼了他有些腼腆的性子,为日后恢复高考后能够走进大学校门、走上工作岗位、从事业余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。
1978年,姗姗来迟的机会终于光顾了有准备的他。“那时,我已经离开了学校,调到矿里的生产科,从事测量绘图工作,在一次义务劳动中不幸受伤,三处骨折,只好在家休养。这一年,高考恢复,我便趁着养伤的机会再度拿起课本。”当年的高考,矿里有一百多名职工、老师和学生参加,只有赵剑华过了录取线。虽然迟迟没有接到通知,但母亲坚信儿子一定能考上,早早准备好了所有行李,只待东风。从盛夏等到寒冬,过了线的赵剑华却一直没接到录取通知。当年12月,正当赵剑华退而求其次准备参军入伍之时,那份大学录取通知终于来了。很巧合,这两个喜讯同一天抵达,上午接到了入伍通知书,下午收到了入学通知书。“入伍还是入学,家里隆重地开了会,最后,选择了入学。”赵剑华说。母亲说不出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”这样的理论,但她力挺儿子读书。而事实也证明,读书,可以造就诗人。
1981年,赵剑华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包钢固阳矿中学当老师。他戏言:“从一个矿里走出来,到了另一个矿。”而正是这单调得有些荒凉寂寞的矿,给了他无限的创作空间。这时,赵剑华已不满足于读诗,而是产生了写诗的念头。“说到创作,我觉得有一个老朋友不得不提,那就是我的同学、我市著名诗人白涛。我还没有开始写诗,他已经小有名气。一次,他来矿里看我,对我说,想写就写吧。回去之后,就不间断地给我寄一些诗歌杂志,推荐我读一些诗集。”1982年,赵剑华的第一首诗《钢铁大街》发表于《包钢日报》副刊。“当时只是一个尝试吧,也没抱多大希望。仿佛是很久之后,一个同事说在报纸上看见了我写的诗,我很激动,但因为时间过久,我始终没看到处女作的真容。”20年后,赵剑华已是誉满全区,才在原《包钢日报》副刊编辑张树宽的协助下看到了自己已泛黄的作品。版面的一角,短小的八行诗,清晰地写着他的名字。赵剑华说,也正是这一个小小的鼓励,让他有了今天的成绩。
赵剑华坚信,诗人的创作源泉来源于生活。对生活的观察和触碰,就是灵感的来源。离开固阳矿,赵剑华调入包钢烧结厂,大工业便成了他创作的背景与底色。“面对庞大而沉默的机器,你的沉默显得无足轻重,你以主人的姿态操作它们,自豪在通红的钢铁间显示……”“平炉前,我接过你的探火镜,一种气质使我霎时高大,眼前是一片蓝色的海……”1991年组诗《大工业》发表于《青年文学》诗歌头条,正是这组大气、凝重、恢弘的《大工业》让赵剑华在1993年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“索龙嘎”文学奖,这是三年一届的自治区政府最高文学奖,电视台做了专题采访,同年,赵剑华第一本诗集《钢蓝色》出版。
赵剑华说:“我一直固执地认为,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。1985年,我们30多名酷爱写诗的青年成立了‘呦呦诗社’我们一起创作、一起讨论。提不足、找缺点,有时争得面红耳赤。也是在那时,包头的诗人频出,诗歌创作盛极一时。”“呦呦诗社”,坚持了三十多年,至今仍有《呦呦诗刊》出版。时至今日,赵剑华仍赞成有份量地去写、有难度地去写,既要写,又不能失去对诗歌的敬重,不能随意去写、什么都写。这大约也是他成功的秘籍吧。
“诗人不制造文字垃圾,这就是责任。”赵剑华说,诗人一定要思考,不能全部理想化。一定要用诗人的眼光剖析这个社会,对那些假恶丑的东西,要用针砭、直视的语言鞭笞。这样才能感受到诗歌的正能量,诗人的作品要对社会负责任。
1994年,赵剑华参与组织出版《包钢文学丛书》,以十本小说、诗歌集的巨制反应大工业的辉煌与钢铁人的精神。1995年,丛书获内蒙古自治区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。《工人日报》特派记者来采访,头版头条分析“包钢文学现象”。2007年起,赵剑华出任包头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,为包钢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,钢蓝色的底色不仅是他创作的背景,也让更多“钢蓝色”的文学出现在读者眼前。2013年,北梁改造,包头市作家协会组织作家深入现场采访,赵剑华参与组织12名作者历经近三年时间写出《天地人心》纪实文学作品集,作品获内蒙古自治区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。
2010年,赵剑华参加了在台湾举办的第三十届世界诗人大会,从此连续7届都接到邀请。“那年,台湾的一些老诗人,像余光中、洛夫等都出席了大会。大会之后,我就写了一大组诗歌叫《诗意台湾》。后来又参加了在以色列、马来西亚、秘鲁、捷克、乌兰巴托、印度和我国贵州举办的世界诗人大会。”2016年,第36届世界诗人大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办。赵剑华获得了这次世界诗人大会年度汉语诗歌奖。那天,刚好是他58岁的生日,半生挚爱,终是幸福。回来后,赵剑华创作组诗《布拉格之秋》。
2012年,赵剑华从职场完全退出来,但文学生涯却得以更好的继续。2018年,包头职业技术学院聘他为首届驻校诗人。“这在内蒙古高校中还是首次,我觉得挺好。把诗歌把文学带进校园这也是自己责任感的一部分。”2018年,赵剑华完成了《蓝色东欧》这一大组诗,发表于《鹿鸣》。
时光匆促,一晃之间,赵剑华写诗也有三四十个年头了,他说,从幼稚到不断成熟,曾是一个艰难的过程,而这过程中的快乐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。他说,诗人是用诗歌来和世界对话的人,可无论怎样对话,善良和真诚不可或缺。







